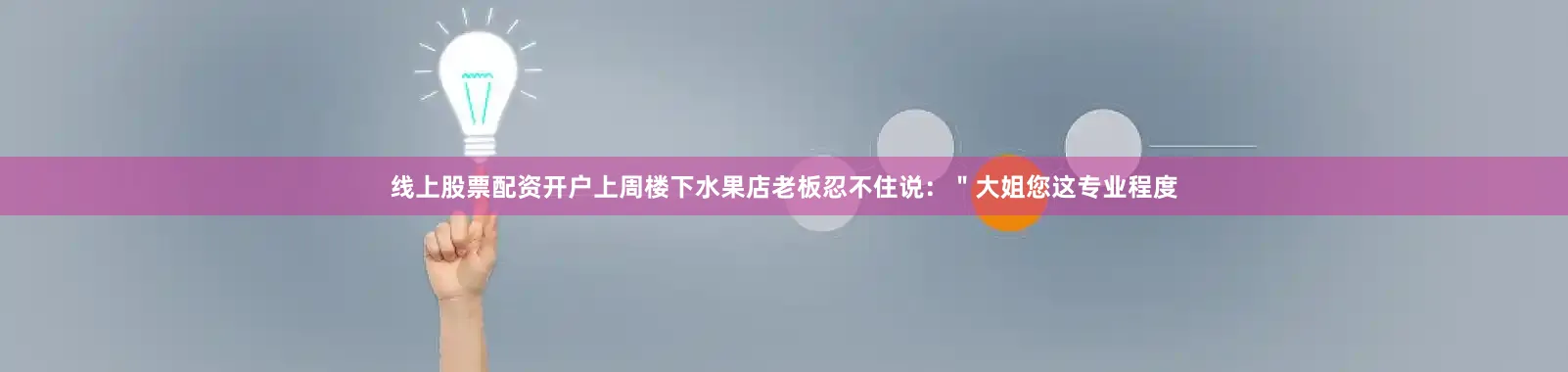我爸是1945年被抓壮丁拉来新疆的。
那会儿他才十八岁,在甘肃平凉老家刚学会种麦子,就被两个穿灰军装的人堵在田埂上,连给我爷爷奶奶道别的功夫都没有,就被强行拉走了。
后来他跟我讲,跟着部队走了十几天才到了兰州,然后一路西行,坐车或步行到了新疆,先驻在迪化(现在的乌鲁木齐)老满城。
那地方我后来去过,现在是热闹的居民区,可我爸说当年就是一片土坯房,风一刮能把人吹得睁不开眼。
后来部队又移防到呼图壁县,番号他到死都没记清——不是记性差,是那会儿兵荒马乱的,父亲又不识字,想着有吃有喝就行,没有过多注意这些。
当时国军部队里的“规矩”:上级军官打骂士兵,比家常便饭还平常。我爸天生耿直,见不得有人欺负人。
有次连长当着全连的面踹一个小兵,我爸忍不住说了句“都是爹妈养的,别太过分”,这下可好,连长当即把他拽到操场,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,打得他嘴角流血,还放话“再多嘴,打断你的腿”。
展开剩余87%那会儿我爸心里就一个念头:这破部队,一天都待不下去。他瞅了个空子,趁着半夜站岗,偷偷往老家的方向跑。
可没跑多远,天就亮了,追兵很快就追上了。连长恨他“逃兵”,竟让人把他脱光衣服绑在操场的老杨树上——那可是大夏天,新疆的太阳毒得能晒脱皮!
整整两天两夜,不给水不给饭,我爸就那么被绑着。他后来跟我说,白天晒得头晕眼花,晚上蚊子能把人抬走,到最后他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,直接昏死过去。
等他醒过来,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废弃的仓库里,周围全是屎尿,老鼠在脚边窜,苍蝇嗡嗡得能盖住说话声。
部队医疗条件差,更别说他一个“逃兵”,没人管没人问,伤口发了炎,咳嗽的毛病从那会儿就落下了根,后来成了一辈子的病根——不管春夏秋冬,他总咳得撕心裂肺,尤其到了冬天,半夜里我常被他的咳嗽声吵醒,心里揪得慌。
1949年9月25日,新疆和平起义,我爸所在的部队编入了解放军序列。
这对他来说,是这辈子最“解气”的事——再也不用看军官的脸色,不用怕随便被打骂,部队里讲的是“官兵一致”,连吃饭都能和班长坐一张桌子。
当时部队还教战士们练习写字识字学文化。我爸就此认识了不少字,能够独立地读书看报了,摆脱了文盲。后来父亲说起这件事总是一脸的骄傲。
没多久,兵团搞大生产运动,人人都要下地干活,开荒、种粮、栽棉花,要在戈壁滩上造出“粮仓”。
可我爸的身体实在跟不上:咳嗽越来越重,干一会儿活就喘得不行,连扛个锄头都费劲。部队领导看他这样,就找他谈话,说“你这身体,回原籍老家吧,也算落叶归根”,还给了他路费和安置费。
换旁人,可能早就答应了——毕竟老家有亲人,不用在新疆受这份苦。
可我爸一听就急了,拍着桌子说“我不回!”领导劝他“你这身体,在这儿也是遭罪”,他梗着脖子说“起义的时候我没跑,现在搞生产,我更不能当‘逃兵’!我就是死,也要死在新疆的地里!”
他说这话时,眼泪都快下来了。领导看他态度这么坚决,只好妥协,把他安排到“四角杂勤”——不用去大田干重活,负责给连队挑水、喂牲口、整理仓库,偶尔帮着给战士们缝补衣裳。
我爸干起活来,那股认真劲儿没人比得了。挑水的时候,桶里的水从来不会洒出来;喂牲口时,总是把料拌得匀匀的,连马鬃都梳得顺顺的;仓库里的东西,他按种类摆得整整齐齐,哪个袋子里装的是麦子,哪个是玉米,闭着眼睛都能摸对。
更难得的是,他还粗懂几句维语——在呼图壁的时候,跟当地老乡学的,能简单唠几句家常。
有次连队跟附近哈萨克族老乡换粮食,语言不通卡了壳,我爸凑过去,用半生不熟的维语加手势,居然把事儿办成了。领导看他机灵、责任心强,还愿意帮人,就推荐他入了党,后来又提拔成了干部,调到石河子机耕农场一分场管后勤,当起了管理员。
有次一个河南来的支边青年想家哭了,我爸把自己的白面馒头塞给人家,还说“别哭,新疆就是咱的家,好好干,以后啥都会有的”。
我那时候不懂,只觉得我爸特厉害,跟个“大干部”似的,后来才知道,他不过是把自己受过的苦,都变成了对别人的暖。
垦荒初期,部队从苏联引进了不少新蔬菜,茄子就是其中一种。
那会儿大伙都是从老家来的,别说种茄子,好多人连见都没见过——有人说“这紫不溜秋的东西,能吃吗?”
有人说“说不定得剥了皮煮,跟土豆似的”,你一言我一语,没人敢先尝。
我爸那会儿是后勤管理员,看着一堆茄子没人动,心里急了——总不能让这些菜烂在地里吧?
他一拍胸脯,大声说“我吃过!我教你们怎么吃!”其实他哪吃过啊,不过是想帮大伙解围。
只见他拿起一个紫茄子,洗都没洗,“咔嚓”就是一大口,嚼了两下,脸瞬间就变了——那生茄子又涩又苦,跟啃树皮似的。他想咽,咽不下去;想吐,又怕丢面子,只好硬着头皮嚼,五官都拧成了地里刚拔的麻花。
周围的人先是愣了,接着“哄”的一声全笑了——有人笑得直拍大腿,有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,连旁边喂猪的老周都放下猪食瓢,凑过来看热闹。
我爸实在忍不住,“噗”的一声把茄子吐在地上,脸比茄子还紫,挠着头说“嗨,这玩意儿,生吃不行,得煮!”
后来这事成了连队的“经典笑话”,每次有人提起,我爸都跟着笑,一点不生气。
我小时候总拿这事逗他,说“爸,你那会儿咋那么傻,没吃过还装吃过”,他摸着我的头说“傻啥?要是没人先试试,大伙都不敢动,那菜不就浪费了?笑就笑呗,总比糟蹋东西强”。
现在我每次吃茄子,都会想起这个笑话,笑着笑着就鼻子酸——我爸哪是傻,他是怕大伙犯难,想替别人扛一点,哪怕自己成了笑话,也不在乎。
我爸当了干部,按说条件不算差,可那会儿没姑娘愿意跟他。为啥?还不是因为他那身体——常年咳嗽,看着就像个“病秧子”,干不了重活。
山东来的姑娘一听“老咳嗽”,摇头;湖南来的姑娘一听“体力不行”,也摆手。
为这事,我爸自己也很自卑,可他心里还是盼着有个家——累了能有人递杯热水,病了能有人端碗热粥,尤其到了晚上,看着别人家里亮着灯,他总一个人坐在门口发呆。
后来没办法,他只好托老家的人帮忙找对象。巧了,同村有个女人,是我妈的同学,没上完学就跑到新疆工作,知道我爸的情况,也知道我妈家的情况,就把我妈介绍给了他。
我妈后来跟我说,第一次见我爸,就觉得他“看着老实,不像是坏人”,就是咳嗽得厉害,说话都得停两下。
我外公一开始还不愿意,说“这娃身体太差,怕以后撑不起家”,可我爸跟我外公掏心窝子说“我虽然身体不好,但我肯定对您闺女好,对家里好,绝不委屈她”。
就这么着,我妈跟着我爸来了新疆。
后来我问我爸,当初怕不怕我妈反悔,他说“怕啊,可我能咋办?只能用一辈子对她好,证明她没选错”。
60年代中期,我爸被调到总场加工厂。那会儿他身体好些了,工作也顺风顺水,本以为能安稳过日子,可没几年,特殊时期就来了。
因为他当过国军壮丁,有人就揪着这事不放,说他“历史有问题”,天天让他写检查,开会批斗。
我爸耿直,不承认自己“有问题”,就被人拉到台上站着,低着头挨骂。
有次批斗会开了整整一下午,他回来时,衣服上全是脚印,咳嗽得连饭都吃不下。
那段日子,家里全靠我妈撑着——她既要照顾我们兄妹几个,还要偷偷给我爸送药、洗衣服,晚上等我们睡了,再陪着我爸说话,怕他想不开。
我爸后来跟我说,“要不是你妈,我真撑不过来”。
好在特殊时期结束后,我爸官复原职,日子慢慢好了起来。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,54岁那年,就提前病退了——按规定,病退的生活费比正常退休少一大截,可他没抱怨,只说“能活着陪你们,就够了”。
退休后,连队给职工分了块地,让自己盖房子。我爸非要自己动手,说“自己盖的房子,住着踏实”。
那会儿我才十几岁,跟着他一起忙:天不亮就去苇湖里打苇子,芦苇叶子割得手全是口子;然后去连队批的树林里砍树,扛着椽子往回走,累得满头大汗;回来还要自己打土块,和泥、脱坯、晒坯,每一块土坯都得砸得实实的。
房子盖好那天,我爸站在门口,笑着笑着就咳了起来,咳得直不起腰。没过多久,他就彻底病倒了,住进了医院,这一住就是好几年。
我记得每次去医院看他,他都拉着我的手说“房子盖好了,你们以后有地方住了”,眼里满是欣慰。
其实我知道,他是为了我们——他怕自己走了,我们没地方住,所以硬撑着把房子盖好,哪怕耗尽自己最后一点力气。 还有件事,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有次我爸赶着借来的马车,带我去别的连队买红薯——那会儿红薯金贵,能改善伙食。
晚上回来时,天已经黑透了,土路坑坑洼洼,马车跑得有点快。
突然,车轮“哐当”一声掉进了坑里,我爸没坐稳,一下子被颠下了车。
我当时才9岁,吓得直哭,坐在马车上不知道该咋办。可我爸愣是没顾上疼,死死地拽着缰绳,嘴里一个劲地吆喝“吁——吁——”,那马受惊了,往前跑了几步,被他拽住了。他爬起来,胳膊上擦破了皮,裤子也撕了个口子,却先问我“你没事吧?吓着没?”
后来我才知道,他摔下去的时候,膝盖磕在了石头上,疼了好几天都不敢说,怕我妈担心。
那会儿我不懂事,只觉得我爸厉害,现在想起来,才明白他当时有多怕——怕马跑了,怕我出事,怕我们连红薯都运不回去。
我爸60岁那年,还是走了。
现在我每次回老房子,都要去看看那间他亲手盖的房子——墙还是那么结实,椽子也没变形;厨房的灶台上,还放着他当年用的铁锅;院子里的那棵榆树,是他当年栽的,现在已经长得枝繁叶茂,夏天能遮一大片阴凉。
有时候我会做茄子吃,每次都会先煮得软软的,再炒得香喷喷的,然后想起他生吃茄子的傻样,笑着笑着就哭了。
我总觉得,他还在我身边——还在赶着马车带我去买红薯,还在咳嗽着说“没事,爸不累”。
我爸这辈子,没干过啥惊天动地的大事,从国军壮丁到兵团干部,从被打骂的小兵到撑起家的男人,他吃过的苦比新疆的戈壁还多,可他从没抱怨过,从没放弃过。
他就像兵团地里的一棵白杨树,扎根在戈壁上,风刮不倒,雨淋不坏,默默守护着自己的家,守护着这片他热爱的土地。
发布于: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盛达优配官网-实盘配资网站-按月配资开户-个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